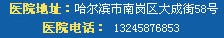一定是特定的缘分,天下着雨,我怀着忧愁,在雨中漫步走近你。
我是熟悉你的,曾不止一次的“拜访”过你,所以我很自然的绕着后山湿漉漉的路,登上了岷郡山。
一路上树叶已经开始败落,灰淡干枯。而今年的麦苗却刚刚盈寸,嫩嫩可食,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的景致。
若说有,当属于山顶庙宇院中的那棵巨大的皂荚树。它果实累累,叶子亮绿,荫蔽着大殿的一角。然而走到近前,却感觉是大殿的一角护佑了这棵千年的古树。
为何会在大殿的背后种一棵皂荚树?第一次去岷郡山我是很疑惑的。
记得那是数年前春天,满山的桃花和槐花香气扑鼻,落英缤纷。而高大的院墙内却显得有些冷清,除了岁寒也不改色的古柏,最有春意怕只是这颗刚刚探芽的皂荚树了。
这不由得让人欢喜。
但我不是特别了解皂荚,只是听父辈们说起过:在没有洗涤用品的过去,可以用它捶打粗衣麻布,去除汗渍。为此,我特意翻了翻文人墨客的笔下,是否有关于皂荚树的诗句,可以用来吟诵的,却发现有不少:比如杨万里“皂荚树阴黄草屋,隔篱犬吠出头来”,又如纪晓岚“微风处处吹如雪,开遍深春皂荚花”等等。
我想皂荚树就种在屋前,对于农家它可以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,对于达官显贵便是向往田园生活的精神寄托而已。
我想当初种树之人也有这寄托吧,毕竟人出三千红尘,哪能一丝一缕都不带纤尘的呢?不过,现在想来自己当初的想法得确是欠妥当的。这都源于我偶然间读到了一首诗,是一位名叫王逵的诗作:
修炼曾君些,传闻固异常。坛留皂荚树,人去白云张。龟得胎中息,神藏肘后方。辽东鹤未返,华表夜苍苍。
“坛留皂荚树,人去白云张”,没想到诗中留下遗树——皂荚树,种植者竟然是一位飞升成仙的得道之士,这不禁让我感到惊讶。但转念一想,仙道飞升与种一棵皂荚树究竟能有多大的关联,充其量就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、“牵强附会”罢了,何况修仙之道本就玄妙难言,说不定就是为了“为赋新词”而创设的意境,也不得而知。
再之后我看到了另有一首诗,它是徐凝之作:
九幽仙子西山卷,读了绦绳系又开。此卷玉清宫里少,曾寻真诰读诗来。紫河车里丹成也,皂荚枝头早晚飞。料得仙宫列仙籍,如君进士出身稀。
初读此诗,我震惊不已,然而震惊之余便是懊悔,感觉自己很肤浅,“误解”了一向低调的皂荚树!
曾经我浅显的以为:皂荚树只是仙道遗留之种,借着“一人得道”的几分运气,便诗留华章,有了几丝仙气,可现在看来,事实远非如此。
从诗句中试解,皂荚树下竟是仙家的“道场”,我临窗苦思,幽幽闭上双眼,竟然依稀可见:
皂荚树春华之下,香气氤氲,仙家气定神闲,静心以洗涤心中之污秽;皂荚树秋实自落,仙道扫叶间无意捡起几枚皂荚净衣,洗去身上之尘垢……谁曾想仙家竟以这世间之物,洗去这世间之尘,以傍身之法,守护这世间安详。
如此想来,这曾经小院栽种俗物,远离了俗世,成为不俗之物;曾经繁忙的皂荚树下,竟是修身之法门,知行合一之道场。
此刻大雨中,我孤身站在皂荚树下,想起曾经我对皂荚树的“误解”,顿时思绪万千,感觉天地苍茫,回想起千年前种树之人——萨真人。
当年他离开的故土,不辞辛苦,孤身到江西龙虎山拜访虚静天师虚心求知,学成之后,他又以传道为业,以书符救世,大显道法与神州之上。由此,他稳健的步伐,踏遍神州的山山水水,处处留下了他救死扶伤——修身修道之“行迹”。
晚年他返回故土,主持岷郡山,于是重修庙宇,募化十方,为救治四方感染瘟疫的民众,设立医馆,以一己之力在皂荚树下护佑四方,直至羽化。
仙人已逝,然灵气善存,千年古柏悠然,千年皂荚繁满,山下盛世如愿,神州故土安详。
………
我想我是幸运的,曾看到过岷郡山上皂荚树花开,曾嗅到过岷郡山上皂荚花香,曾捡起过岷郡山上皂荚熟透的果实,曾守望过岷郡山皂荚树的春意……
在我的内疚和不安中,看似普通皂荚树呀它已经默默给了我答案,解了我之心头忧,让我知道人应该像皂荚树一样,低调内敛去淬炼自己的身心,像皂荚树那般去身体力行做一个致良知的君子。
所以,我时刻仰望着你——岷郡山上那棵皂荚树。
注:岷郡山位于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城南,漾水河畔,俯瞰伏羲广场。从城中而望,东南连横岭来山,前有两棵参天古槐,一对雄伟石狮,一座阔门庙宇,乃是北宋期间萨真人的羽化飞仙之处,自古香火鼎盛。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zz/8841.html